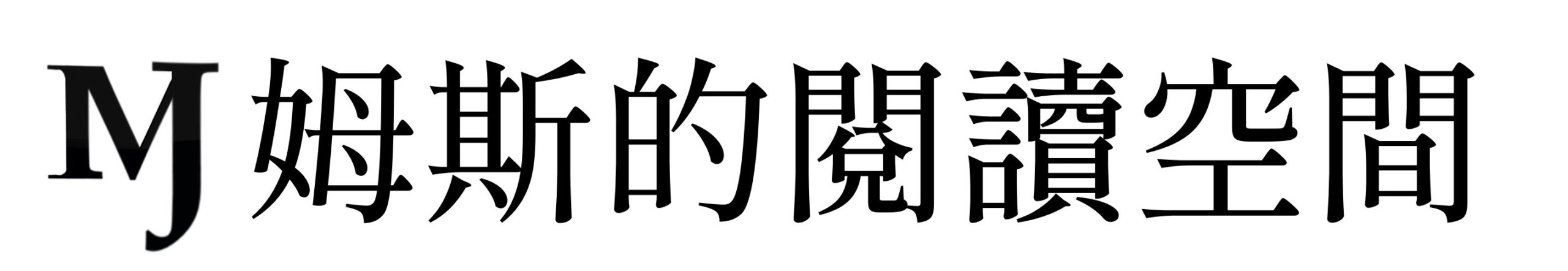《監獄中的哲學課》的作者安迪.維斯特從 2015 年起,開始前往監獄開設哲學課程。走過種種監獄現場的他,將這些經歷寫成了這本書。除了記錄與囚犯的互動與監獄內的見聞,維斯特也藉由回顧這些經歷,深入剖析自己的出身與內心掙扎,是一本切入角度相當獨特的回憶錄。
起初我以為這是一本藉由深入社會底層進行教學,進而反思自我、獲得救贖的書;然而翻開書後才發現我錯了。書中的內容大多不像我原本想像的那般正向,反而讓我讀來感到些許憂沉。儘管激發了許多思考,很多時候得到的不是清澈的理解,而是一種混沌。讀完後我仍是喜歡這本書的,只是感受很複雜。以下,且聽我娓娓道來。
Table of Contents
【監獄中的哲學課】
維斯特的哲學課很活潑。許多時候,他不會直接給出答案,而是丟出一個主題,讓囚犯們輪流發言討論。許多教學現場的互動都相當有趣。
比方說,囚犯們可說是臥虎藏龍。例如,當維斯特講解洛克的理論時,一名叫馬卡的囚犯就打斷他說:「你講得不太對。」並接著說到:「洛克不只談記憶(memory),他更強調意識(con-sciousness)。幾分鐘後,一位遠距的「學生」又指出,盧梭可能不會同意洛克的觀點。
不過,有些時候情況也會有點失控。像是一名熱愛讀書的囚犯基斯,就一路從莎士比亞談到量子物理,發言慾強到讓維斯特很想打斷他(笑)。
討論也可能演變成爭執。例如,有次維斯特談到傑瑞米.邊沁「幸福 = 快樂」的說法時,一名叫薩瓦爾多的獄友滔滔不絕地發表高見:「在監獄裡可以很快樂,你知道嗎?……我一輩子都從未感到無聊。我的腦子裡沒有牢房,別人總對我說:『薩瓦爾多,你為什麼老是笑得那麼燦爛?』我告訴他們……」這時,一名叫吉姆的囚犯打斷他,指著白板上的邊沁說:「他設計了全景監獄。」場面瞬間尷尬。
課堂有時也會陷入混亂。像有次,維斯特談到《等待果陀》,並提到劇本中的啼啼與哭哭用打架來殺時間,結果一名獄友就說,昨天有兩個牢房裡的傢伙為了搶電視節目而打架。接著,大家竟開始爭相分享各自的追劇心得。雖然維斯特試圖把話題拉回來,但聊到嗨的囚犯根本不理他,他只能默默等大家聊完再繼續課堂。
【監獄百態】
透過哲學教學,維斯特也看見了監獄的複雜樣貌。
例如,在監獄中,犯罪其實是有階級之分的。某些囚犯被稱為「易受襲擊的囚犯」(Vulnerable Prisoner,簡稱 VP)。許多 VP 是因為性犯罪而入獄,他們需要特別隔離管理。如果讓他們和其他「主流」囚犯混在一起,很容易就被打到頭破血流。維斯特也發現,許多主流囚犯會主動談自己的犯罪紀錄(像是驕傲地自稱毒販),但 VP 們幾乎不談自己的罪刑。若是不小心碰觸這個話題,他們不是否認,就是自我貶抑或傷害。
此外,書中對女性監獄的觀察我覺得也很有意思。一名典獄長告訴維斯特,有超過一半的女囚犯曾遭受家暴。她們之所以坐牢,往往是為了幫男友吸毒。也有不少女囚在青少年時期就被人口販子賣掉,成了性工作者。
而女囚犯的上課情況也與男囚犯大不相同。維斯特說,她們會各自坐在圍成圈圈的椅子上上課,有些人甚至會幾乎坐在彼此的大腿上。不像男囚們彼此不熟、常要靠維斯特「湊成一團」,女囚們則早已自成小集團。
另外,維斯特也對監獄存在本身提出了討論。例如,書中有一名叫盧卡斯的囚犯,正在服「保護公眾監禁」的刑期。因這項刑罰入獄的人,至少會被判五年徒刑,但國家(此處指英國)有權關他們長達九十九年。這套制度於 2005 年推出,原本是為了處置最嚴重的犯罪者,但後來也有人因為竊盜或偷手機而被判這項刑罰。雖然這制度已於 2012 年廢除,卻不溯及既往。像盧卡斯這樣的人,根本不知道自己會被關到什麼時候。
這讓我想起書中一段獄警們的對話。一名叫巴柏的獄警說,囚犯只要年滿二十二歲,一生就毀了。他們會一次又一次地回來坐牢,所以最好把他們關在牢裡面。另一名獄警拉馬爾則反駁:「如果你不給人改變的機會,他們永遠不會改變。」巴柏笑回:「我曾經也像你一樣,但等你和我一樣在這裡工作這麼久後,你的想法就會改變了。」
說到底,監獄的存在究竟是為了什麼?是為了幫助囚犯矯正,還是僅僅是關押他們?理性上我們都知道答案應該是前者,但現實常常背道而馳。書中維斯特的這段話讓我陷入沉思:
我希望我能推倒這種建築,打造另一個更有想像力的建築,一個要能治癒人而非僅是收容人的地方……然而,這棟建築依然矗立著。
說到底,大家對於犯罪者還是存在極大戒心吧。一名叫布萊克的囚犯就說,他在監獄裡比外面更容易表現友善。因為每當他試著在外面做好事或展現友善時,人們都會用奇怪的眼人看著他,覺得他在打什麼壞主意。書中的他對維斯特這麼說:
不管我在外面做什麼,我都是有前科的傢伙。這就好像我在外面的世界中只被允許處在 2D 的狀態。但在這裡,當我為第一次入獄的人提供建議,或者我拿水壺給別人喝水時,我是在幫助另一個人。我的善良不會被扭曲。當我在這裡時,我能以 3D 的形式存在。
【從監獄教學找自己】
除了談論監獄中的教學,維斯特也透過這段經驗,深入挖掘自己過去的經歷與內心的陰影。他的爸爸、叔叔和哥哥都曾入獄。即便他因為遇上哲學而走上不同的道路,但這樣的背景仍深深影響著他,留下難以癒合的內在傷痕。
在維斯特出生那年,他父親就入獄服刑十八個月。童年期間,父親依然不斷犯案,偷竊、詐欺樣樣來。維斯特於是擔心自己是否也是個「壞胚子」,有次甚至趁爸爸熟睡時,跪下祈求上帝再給他做一次好人的機會。
長大後,這種恐懼感並沒有消失。維斯特說,他腦中總有一個「劊子手」,隨時準備扼殺他所擁有的一切。對書中這段談他越來越像父親的段落印象很深:
我在三十歲後,開始越來越像他了。我把頭髮弄得蓬鬆,看看是否能改變臉型,但我看起來依然很像他,我的額頭和下巴跟他很像。腦海的劊子手告訴我,我根本無法改變它。
這樣的恐懼甚至發展成一種「入獄妄想症」,讓他總覺得自己會犯罪,接著被捕入獄。劊子手會不停對他低語,說他一定幹了什麼壞事。書中有一拖拉庫這樣的妄想情節,例如他進監獄前被保全搜身時,會妄想警衛會從他背包中搜出一公斤海洛因。有一段時間,他甚至不斷擔心自己會燒掉房子,總是在出門後跑回家確認是否關好爐火。
書中這段恐懼症發作的段落,看得我心很疼:
我的手指捲曲了,無法扳直。我打算起床,但雙腿好像變成石頭,僵住而無法移動。我想到廚房裡的刀子。劊子手說我會拿刀去傷人。他說我也許已經傷過人,而且已經封鎖了這樣記憶。
相較於父親,維斯特談叔叔和哥哥就相對溫暖些,但仍然藏著傷。他對監獄很好奇,所以會去奶奶家聽弗蘭克叔叔講述他犯罪或坐牢的「趣事」。這是他與叔叔維繫關係的方式:
我一遍又一遍聽著這些故事,就像聆聽早已熟記歌詞的歌曲……我和叔叔能維繫關係,就是他會跟我說故事。儘管我經常感覺我們之間有一堵牆,但我認為他跟我講故事時,總有一條想像的線將我們串在一起。
維斯特也喜歡聽哥哥傑森講故事。不過傑森不像叔叔那樣樂於分享,他總得慢慢「挖掘」出來。(我特別喜歡他哥腿被刺的那段,好痛又好笑。)
書中提到,傑森的入獄多與吸毒有關,這也讓維斯特對喝酒與吸毒等「玩樂」行為特別敏感。他寫道:
當哥哥被關在監獄時,我要是尋歡作樂,會讓我覺得自己很討厭。為了傑森,我滴酒不沾。這是我在他不在時愛他的一種方式。
因為這樣的「壞基因」背景,維斯特與犯罪始終維持著一種微妙的關係。一方面,他懷著深深的罪惡感,擔心自己也是個壞人;另一方面,他又對這個反面世界充滿好奇,渴望理解它。這樣矛盾的心態,也成了他走入監獄教授哲學的動機之一。
儘管監獄經常讓他感到痛苦,甚至觸發腦中的劊子手,但他仍願意繼續這樣的工作。書中他這麼說:
在這裡教書如此觸動我,所以我想繼續下去。我不想讓劊子手獲勝。我已經讓他從我身上奪走太多東西了。
而維斯特也確實從這樣的教學互動中得到了些什麼。很喜歡書中有位囚犯對他說的:「學哲學很好,讓我知道我還有自己的想法。」這讓他理解到,自己所做的不僅是見證失去的東西,還可以幫助人看清自己。
【後記】
這本書給我的感覺,更像是一部以監獄教學為外衣、實則深入自我探索的散文集。儘管如此,我依然特別喜歡他與囚犯們討論哲學的部分。那不是一種上對下、居高臨下的教學,而更像亞里斯多德式的對話與思辨。讀著讀著,我也不自覺地跟著進入那些問題之中,一起思考。
如開頭所說,這本書和我原本的想像大不相同。雖不乏自救與贖罪的光亮時刻,但整體氛圍更偏向灰濛與壓抑。雖然是好看的,卻也讓我讀得有點心悶。而且直到最後,維斯特也沒有給出一個正向、明確的收尾,只留下大片的思索空白。不過,也許這正是維斯特最後的一堂哲學課吧——接下來,就是我自己的事了。
你可能也會有興趣的文章:

↓↓也歡迎大家來追蹤〈姆斯的閱讀空間〉的臉書、哀居和Podcast↓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