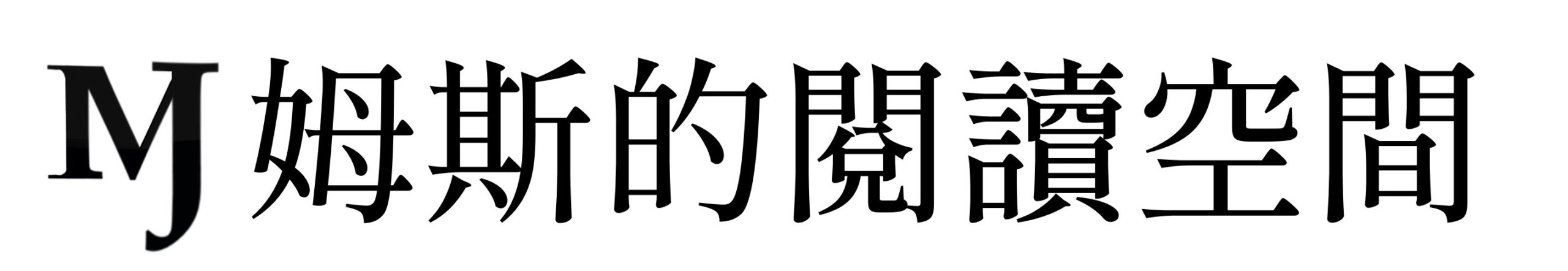《啟程,同感脆弱的世界》是本遊記。作者鍾偉倫在書中紀錄了他探走菲律賓、衣索比亞、伊朗、孟加拉、哥倫比亞、厄瓜多、斯里蘭卡和阿曼等八個國家的所見所想。作為遊記,裡頭自然有不少「遊」點;但除此之外,鍾偉倫也引申出許多個人的反芻思考,發散出不少有意思的想法,相當耐人尋味。以下聊些心得。
Table of Contents
【微冷門的國家們】
鍾偉倫在此書中造訪的都是較冷門的國家。如他說的,這些國家既不因戰亂而受人注目(如阿富汗),也非傳統定義上的強國(如英國),更不是典型的觀光熱點(如義大利)。而這些國家的周邊,也往往有更容易成為旅人「優先選擇」的鄰國:哥倫比亞旁有以馬丘比丘聞名的祕魯,阿曼的旁邊的則有近來發展火燙的阿聯酋。
然而,透過鍾偉倫的探撥,我仍看見許多迷人的風景。就景觀來說,我印象最深的是位於衣索比亞的爾塔阿雷火山——火燙的景色令人窒息:

此外,我也從中學到了許多新奇的在地冷知識。例如「衣索比亞時間」:在當地,他們的零時並非午夜,而是我們的上午六點;又如伊朗人一天要喝七、八杯茶,且會口含方糖後啜飲;至於將咖啡視為國策(猶如半導體之於台灣)的哥倫比亞,則只允許栽種一百多種最純正的阿拉比卡咖啡。
書中各地的風土人情也相當有趣,其中,孟加拉的「壅擠」最讓我印象深刻。由於人口密度高且基礎交通建設不足,眾人只能一同到路上拚搏——只要一有空隙,大家就會像鯊魚看到魚群一樣迅速將其填滿;在這裡,步行與人力車或汽車的速度幾本沒有差別,且無輕軌或地鐵等替代選項。鍾偉倫形容,這是一座「在通勤上眾生平等」的城市。
除了新奇,還有驚悚。書中提及的菲律賓「迷魂黨」讓我感到背脊發寒:他們擅長先取得被害人信任,再以強姦藥片迷昏取財。常見的作案組合是三人女性小隊(也是鍾偉倫遇到的,幸好他逃過一劫。):老婦人(指導人與控制場面)、中年婦女(負責聊天)和年輕女子(實習生)。這邊放上犯罪老婦人的照片,讓大家可以提防提防:

【脆弱的世界】
鍾偉倫將自己書中探訪的國家稱為「脆弱的世界」。他坦言,許多國家並不算弱小,之所以用「弱」,是因為中文沒有更好的形容詞,也許英文的 Fragile 更精確些。在他的眼中,「脆弱的世界」指的是較少報導或宣傳,且因經濟發展或政治、國際局勢等因素,使驅動我們到訪的那些事物難以長久維持的國家。
前面提到的爾塔阿雷火山就是如此。鍾偉倫指出,這裡的火山岩相當脆弱;若在其他國家,這類景點通常會設置隔離措施以保護;然而在此地,只要能忍受硫磺氣體,就可自由行走。
布滿了整片經歷千萬年而形成的結晶,就這樣被為數仍不多的遊客、嚮導和當地人隨意踐踏。
對書中的這段話很有感:
貧窮國家的脆弱性,除了始終貧窮而無力抵禦衝擊,還存在於,為了力爭上游而急於拋棄那些值得被保留的美好。
在這樣的脆弱國度生活,自然不容易。鍾偉倫在序中提到,這次啟程的目的之一是想觀察「那些和我一樣未必極端困苦,但也為生活掙扎的普通人」。他認為,脆弱的世界最能考驗人類的適應力,而他深深被這種生存之堅韌折服並認同。
在菲律賓,他看到為謀生計,在暴風暴雨中帶他深入深山觀賞「木乃伊」的嚮導,因而感嘆:「他也和我一樣,都只是被釘在自己土地上的營生者。」在斯里蘭卡,他則看到了海灘上為整理魚貨,腰部永遠彎成九十度的老婆婆。

就連長灘島的網紅也成了鍾偉倫的「觀察」對象。他形容長灘島彷彿是尚未成氣候的網紅訓練營(更高階的地方小網紅去不了),許多小網紅會在這度假勝地自拍、直播,將旅遊生活展現給大眾。起初,他對此頗感不耐,甚至說他們是「在這海灘詮釋搔首弄姿,對著小螢幕自言自語」的人。但他旅伴卻點醒他:「這不就是你想要的嗎?你不是想知道人們如何掙扎著求生?這些網紅,這就是他們的謀生方式啊。」

不過,要說掙扎,最令我印象深刻的,莫過於衣索比亞鹽田中切割岩塊的工人。他們得將鹽磚削成五至七公斤,再用駱駝馱往約兩百公里外的默克雷(衣國第二大城)賣給當地商人。每塊鹽磚商人以一百 Birr 買入,再以兩百 Birr賣出。但削磚工人只能拿到五 Birr(約台幣七元五角)。
鍾偉倫不解地問嚮導,為何工人不自組車隊運磚,反而任由駱駝商與商人剝削?嚮導回說,他們賺得錢只夠當天花,哪來的錢僱卡車。而且這些鹽塊不用成本,他們只要切磚就能領薪水。他不放棄地再問:「但是這些鹽塊總會有用完的一天啊。」嚮導回說,鹽田的深度有兩公里,再挖幾百年也挖不完。
鍾鍾偉倫將此稱作「免費資源的詛咒」:若沒到真的活不下去,沒人會想到要改變。貧窮會窄化一個人,甚至一個民族的思維。他因此反思:
我們以為全靠自己的努力,形塑了周遭的世界為己所用。但是真相經常是,命運的隨機分配對我們來說,影響更大。
【旅行的意義】
除了向外探索,鍾偉倫在書中也不斷向內思索:對他來說,旅行的「意義」是什麼?或者換個角度問:為何要「啟程」?關於這主題,書中雜散地聊了許多。
要長期在陌生的異地遊走,對許多人而言不是件容易的事。然而在序中,鍾偉倫卻認為,在他人眼中看來的「起程勇氣」,不過是聽見遠方召喚後,自然做出的回應罷了。他甚至半戲謔半認真地說:
關於勇敢上路或自我探索這些個人議題,夠了。連出去玩都要勇敢,這實在說不過去。在我看來,留在台灣掙扎工作養兒育女,那才叫勇敢。
當然,旅人百百種——也有人巧妙地將旅行體驗包裝出售,讓原本的玩樂成為謀生技能。例如,書中提到一位資深旅人X:
X在三十歲左右恢復單身,這樣的小偏離讓她開始了一年左右的大旅行。回台後,她把旅行的愛好,跟企劃、行銷文案等技能結合,寫成了啟發成千上百與她一樣,在相同交叉點遇到相同抉擇的「輕熟、小資」們心有戚戚焉的暢銷旅遊書。
於是乎,旅行成為了一種可「販售」的專業。這種作法當然沒有不好。然而,旅行對鍾偉倫來說並不只是這樣的東西。書中他如是說:
我們如今更加關注,旅行是否可以跟所有事物一樣可以交易。我們拍影片、分享照片、開分享會、出書。總而言之,將經驗變現。這沒什麼不好。只是我始終沒有忘記,旅行的初衷,總是涵在那些能被交易之外,沒有辦法跟任何東西交換,且難以估量其價值的事物。
對他而言,更重要的或許是「體驗本身」。這體驗不必然是親眼見到某個著名景點,也可能是在旅途中獲得某段難以預期的經歷。如他說的:
景點,不過是出發的藉口。
看到所欲之物的美景,只佔經驗的一小部分。錦上添花固然好,若狀況未如預期,經驗仍會緊跟著你,成為你血肉的一部份。看到景點比起體驗過程來說,往往不是那麼重要。
也因此,書的最後他有了這樣的結論:
常常旅行到了一個景點,才發現那裡還有三十個景點尚待探訪。我們要的,並不是把這些地方都走完。
有時候,只要知道這世界是如此大得超乎我們想像,就夠了。
【後記:關於旅行?關於閱讀?】
我其實不是一個特別熱衷旅行的人,這本遊記雖然讓我看得十分新奇,要我像鍾偉倫那樣親身造訪恐怕難度不小(笑)。要說我最喜歡本書的地方,反而是他對旅行的各種思考。很多地方都很犀利,例如他對「首都」的評價:
去過越多地方,旅行所看見的事物就越像是一種拼裝。太陽底下無新事,所有被認為是新的東西,都是舊事務的比例混合。在首都,尤其明顯。所謂首都的樣子,時常只是各種舶來品拼湊。
又如他論「殖民地」風格:
就我的觀察,那會是一種歐洲對於亞非、進步對於落後、溫帶對於熱帶的權力關係,具體呈現在眼睛看得到的地方。而當殖民的權力散去,那將會變成一種把我的故鄉強加在你的土地上,卻無法體抗你的氣味逐漸滲入的一種,溫柔。
他對旅行本身的思索亦相當耐人尋味——書中有段話道:
旅行,並不只關乎取悅自己。我們選擇去哪裡、如何前往、如何消費,這一切都表明了我們對世界投下的一票:旅行,是希望景點只要完全取悅我們就好,還是能夠和當地產生連結,是以一種細水長流的方式互動?
突然發現,或許閱讀與旅遊很像吧?都是自我與世界的交互體驗,只是前者具象於景色風景,後者抽象於書中世界。而這樣的體驗,往往是很個人且獨一無二的,無法簡單與他人分享。
因此,對於書中談將旅行作為「交易資本」的段落,我特別有感。在自媒體興起的時代,不僅旅遊,閱讀也成了可交易的資本;許多說書人包裝心得,讓閱讀成為了一種能「變現」的專業。這樣當然沒有不好,但我仍相信,閱讀最動人的,還是在於那純粹的體驗本身。很喜歡鍾偉倫說的:
我所信仰的,是藉由旅行,創造豐富的體驗。其中一定會有什麼事物,會因此撬動、鬆解開來。
閱讀對我來說也是這樣的存在吧!
希望透過我的分享,能邀請大家也走入這些書中世界,並找到屬於自己的體驗與感動——我是這樣期盼的!
你可能也會有興趣的文章:

↓↓也歡迎大家來追蹤〈姆斯的閱讀空間〉的臉書、哀居和Podcast↓↓